
作者简介: 武亦文,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洁琼,武汉大学大健康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文章来源:《保险研究》2022年第11期
一、问题的提出
置身现代风险社会中,需要努力防范及化解风险,维持生活稳定有序。保险的作用在于汇集社会成员个人力量成立风险共同体,于成员发生事故时给予经济补偿,是现代社会转移及分散风险的重要方式。投保人投保的主要目的在于事故发生时能够使受益人或被保险人获得保险赔付以弥补损失,此种目的凸显于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意外伤害保险之中,关乎被保险人近亲属的生活的维持,意义重大。索赔方能否获得保险赔付的关键在于认定引发损害的原因是否落入承保范围,须首先运用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判断危险是否属于保险法上引发损害的“原因”,其次判断“原因”是否属于可保风险,最终决定保险金能否给付。但近年来实务中频频出现被保险人死因无法查明的情况,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搜索“意外伤害保险”及“死因不明”关键词,相关数据达近千条。被保险人死因不明的原因较为复杂,或由索赔方引起,如其在核保前将尸体火化以致无法尸检;或由保险人引起,如索赔方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进行核定,而后者怠于核定致使死因无法查明;或是双方均怠于查明死因;又或是双方均无过错但死因仍无法查明。我国在此问题上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实务中更未形成统一的裁判规则,以致判决结果五花八门,或是支持保险公司判决索赔方自行承担不利后果,或是判决保险人给付全部保险金,又或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判决保险公司按比例给付保险金。此类案件共性在于无法判定引发损害的原因为何,更无从判断原因是否为可保风险,以致保险责任的认定呈现出相当混乱模糊的局面。有鉴于此,本文将对意外伤害保险中被保险人死因不明时保险责任承担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我国实务及理论界研究现状,评析利弊,在现行法框架下,借鉴域外立法司法有益经验,探索能够平衡双方利益的统一高效的裁判规则,希望对理论研究与司法裁判有所助益。
二、意外伤害保险中
被保险人死因不明之时
保险责任认定现状及困境
(一)意外伤害保险中被保险人死因不明之时保险责任认定现状
我国保险法在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死因不明时保险责任的认定上立法阙如,目前仅有《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做出了相当模糊的规定,为法律解释留下较大空间。此时法官只能转向保险法中的一般规定或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频发,案件上诉率居高不下。目前就意外伤害保险中被保险人死因不明的责任认定问题,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1.全部支持索赔方
在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死因不明的案件中,有相当比例的判决支持了索赔方的全部诉讼请求,但判决理由各有不同,现归纳如下:一是“死因不明”属于猝死,即为意外伤害。由于双方采用的是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在对“意外猝死”理解不同时,应当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应当认定猝死属于“意外伤害事故”。二是“死因不明”属于猝死,猝死免赔条款无效,保险人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一些保险公司会在保单中事先约定“猝死免赔条款”,由此有的法院巧妙回避了“死因不明是否属于意外伤害”的问题,转而从猝死条款的效力入手进行裁判,首先认定被保险人死因是猝死,再以猝死条款属于免责条款而保险公司未向投保人进行提示并作出明确说明,以致所涉免责条款不生效力,从而判决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三是在索赔方已通知保险人出现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没有在尸体火化前予以核定或告知家属等在核定前不得火化,其怠于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22条规定的指示举证义务而导致保险事故原因无法查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四是保险人在事故核定时出具的《尸检告知书》属于格式条款,实质是对原合同内容的添加,此行为未经过对方当事人同意不能订入合同,因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五是索赔方已经完成资料提交义务,即使拒绝尸检也应获得赔付。即根据《保险法》第22条,索赔方仅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对超出其所能提供证据范围的不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责任转移至保险人一方,由保险人承担证明死因为疾病的证明责任。按照农村风俗以及为了维护死者尊严、亲人感情,索赔方拒绝尸检情有可原,不应过于苛责,其并不违反资料提交义务,且只要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证明资料即可获得赔付。
2.全部支持保险人一方
在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死因不明的案件中,亦有相当比例的判决支持了保险人一方的全部诉讼请求,现将其裁判要旨梳理如下:一是“死因不明”属于猝死,虽然猝死本身具有突然性、非本意性的特点,但由于猝死是由内部潜在疾病引起的,不符外来性及非疾病性特征。所以死因不明的情况不在意外险承保范畴。二是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猝死免责条款,保险人已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已发生法律效力,不予理赔。三是索赔方未能履行通知义务,不应获得赔付。根据《保险法》第21条的规定,索赔方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致使其未能通过尸检等方式来确定被保险人的死因,此不利后果应由索赔方承担。四是索赔方未能尸检,没有完成资料提交义务,不应获得赔付。若保险人在接报保险事故发生后,已告知索赔方如拒绝对被保险人身故原因进行病理尸检将承担不利后果,此时索赔方仍拒绝尸检,根据《保险法》第22条的规定索赔方未能履行提交证明资料的义务,其应对死亡原因是否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承担不利的后果。五是索赔方未能举证证明死因,不应获得赔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索赔方应当承担完全举证责任,即使其已经履行《保险法》第22条规定的证明资料提交义务仍不能认定已经完成举证,在索赔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存在意外伤害事故的情况下,应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的后果,不予赔偿。
3.判决比例赔偿
在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死因不明的案件中,也有法院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采用“比例赔付原则”,综合承保风险、举证责任所占事故原因的比例等因素,酌定赔付比例。但是该司法解释的规定给法官留下的裁量空间过大,实务中对于该条如何适用意见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此条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对于死因无法查明均有过错或者均没有过错的情况。如有的法院认为,索赔方怠于沟通致使死因无法查明,保险人虽发送尸检告知函,但未作进一步解释说明、告知相关程序以及法律后果,且没有对除外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均存在过错,应依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判决比例赔偿。其背后的法理类似于我国传统民法中的“与有过失原则”以及“公平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死因不明的案件一律适用比例原则。有的法院虽然认为由于保险公司未通知尸检而应对被保险人死因不明承担责任,但径直以《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判决保险公司承担80%的保险责任,却没有说明为何要由已经完成初步证明义务的索赔方承担剩余的20%的责任。也有法院在因索赔方拒绝尸检而致使死因无法查明之时,根据比例原则判决由保险人承担70%的保险责任。
(二)意外伤害保险中被保险人死因不明之时保险责任认定困境
通过对被保险人死因不明案件判决的归纳整理可以发现,有些案件的案情相差不大而判决结果迥异。究其原因,或许在于法官及学者对概念、法条理解的偏差。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基本概念混淆
抽象概念是规则体系的基石(卡尔·拉伦茨,2020)。导致被保险人死因不明时保险责任认定混乱局面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不同概念的混淆。在死因不明的相关判决及理论中,中文词语的多义性引起不同概念间的混淆。(1)将“意外原因”“意外伤害”“意外事故”等概念混用:将“意外伤害”作为“意外原因”来使用,如“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所致失能、死亡时”(卓俊雄,2019);将其作为“致害结果”来使用,如“意外原因导致的意外伤害”(韩长印、王家骏,2016);提出“意外事故”的概念,将其作为“意外伤害”的替换概念来使用,如“意外事故应具有外来性、突发性及非自愿性三项要素”(叶启洲,2013);将“意外事故”作为“意外原因”来使用,如“将人之伤害或死亡之原因区分为内在原因与外在事故(意外事故)”(汪信君,2011)。(2)将“死因不明”与“猝死”的概念混用。在被保险人死因不明的案件中,若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或是死亡证明中载明“猝死”,有的法院径直从猝死的定义入手,认为其属于潜在的疾病而判决索赔方败诉,有的法院则认为“猝死”不能简单等于潜在疾病,根据格式条款不利解释规则可以推定为意外伤害。对概念之间关系的混淆可能会影响保险责任的认定,因此需要厘清其基本内涵。
2.保险事故认定逻辑顺序混乱
保险责任认定可能存在两种不同逻辑:先通过因果关系认定规则筛选出法律原因,再通过意外伤害认定规则判断是否落入承保范围;先运用意外伤害认定规则判断众多事件中何为意外伤害,再运用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判断意外伤害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第二种逻辑在学界和实务届不乏支持者。如有法院认为,索赔方提交的证据既不足以证明发生了意外事故,亦不足以证明意外事故与被保险人身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蕴含了“先判断意外伤害的构成要件再判断因果关系”的逻辑。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先找出事件是否具有意外性特征,再判断损害结果是否由该事件导致(韩长印、韩永强,2010)。采第一种逻辑会认为死因不明案件首要的问题是法律原因无法确定,因此会重点从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入手解决问题(刘建勋,2018)。采第二种逻辑的学者会认为案件的关键在于无法判断事故是否符合“意外性”的特征,因此会着重分析意外伤害的认定问题(岳卫,2017)。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保险责任问题定性的混乱,也阻碍了明确、统一的裁判规则的构建。
3.法律适用冲突
首先是实体法之间的冲突。根据《保险法》第21条至22条的规定,索赔方未能履行通知义务、资料提交义务或保险人未能履行提示举证义务的,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但是在被保险人死因不明的案件中,法官在索赔方或者保险人一方未能履行上述义务时仍直接适用《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判决比例赔偿,由此导致法条适用时的冲突。在张玉枝、陶洁等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中,尽管法院认为由于保险公司未通知尸检而应对陶某某死因不明承担责任,却径直以《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判决保险公司承担80%的保险责任,而没有说明为何要由已经完成初步证明义务的索赔方承担剩余的20%的责任。因此有的法院判决认为,根据《保险法》第22条的规定,若索赔方的举证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则不存在保险事故还是非保险事故、免责事由难以确定的情况,《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的前提不存在。由此可见,对于该司法解释不加分辨地适用会引发实体法适用上的冲突。
其次是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冲突。《保险法》第22条规定索赔方提供相关的证明和资料以“其所能提供的”为限,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0条证明义务的规定存在冲突。在被保险人死因不明的案件中,如索赔方已经尽一切努力提供资料仍未能够证明发生了意外伤害事故,那么应以其已经履行了资料提供义务为由判决胜诉,还是以“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将承担不利的后果”为由判决败诉?又如保险人未能一次告知索赔方补充资料,致使资料灭失无法查明死因,法院以保险人未履行一次告知义务判决索赔方胜诉,还是以索赔方未完成举证判决其败诉?实务中的判决各异,由此引发条文之间的冲突。
4.裁量标准模糊
即使法院能够明确《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的适用前提,但是该条的适用仍存在较大问题:“人民法院可以按照相应比例予以支持”中的“相应比例”如何确定?在上述案件中,法院以保险公司没有履行尸检通知义务而判决其承担80%责任,但在类似的案件中,保险公司同样没有通知索赔方尸检,法院以死亡地点、死亡状态、死亡年龄及当时的气候状况认定被告保险公司承担50%的保险金赔付责任。还有观点认为比例的确定应综合举证责任、承保风险所占事故原因的比例等因素(中国保险行业协会,2021)。由于缺乏明确的裁量标准,致使相似的案件中保险金赔付比例相差如此之大,难谓司法公平公正。
三、意外伤害保险中
被保险人死因不明案件
的基本问题厘清
(一)基本概念内涵厘清
1.“意外伤害”“意外原因”“意外伤害事故”等内涵厘清及关系梳理
为更加直观、清晰地呈现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现辅以案例进行分析:被保险人患有血友病,散步时被狗咬伤,之后经过一栋房屋门前,房顶花盆突然掉落砸伤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血流不止死亡。那么何为“意外伤害”,何为“意外原因”?此时须从各个概念内涵着手:首先,“事件”这一概念在意外伤害保险中是指客观上对于损害结果的产生有推动作用的事实,范围最广。案件中“散步”“被狗咬伤”“花盆掉落”“患血友病事实”均属于“事件”。其次,“原因”在英美法中又分为“事实原因”和“法律原因”。“事实原因”或称“条件”,是指经过对事件的初步筛选后,找出的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的客观情况,案件中的“血友病”“花盆掉落”均属于“事实原因”。“法律原因”在近因原则下又叫“近因”,是指引发损害结果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对“事实原因”进一步的筛选。案件中与死亡结果有法律因果关系的事件是“花盆掉落”。再次,“意外原因”概念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我国学界基于英美保险法“意外伤害”的认定规则将“意外伤害”中的“accidental means”译为“意外原因”,意指引发损害的近因具有“意外性”特征。在上述案例中,“花盆掉落”便属于“意外原因”,而血友病属于内在的疾病,并不符合“意外原因”的要求。最后,“意外伤害”或称“意外事故”,此概念较为复杂,但是不论是英美法系或是大陆法系,均认为其中既包含“原因”要素,又包含“结果”要素。我国学者多将“意外伤害”分为“意外”和“伤害”,前者是指上述的“意外原因”,后者是指“损害结果”(刘强、陈禹彦,2015)。上述案例中“花盆掉落致使被保险人死亡”整体属于“意外伤害”或称“意外事故”。
至此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便变得清晰起来,即下图所示:

2.“死因不明”“猝死”的内涵厘清及关系梳理
(1)死因不明的内涵厘清
“死因”一词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疾病分类》的规定,“死因”即指“直接或间接促进死亡的疾病或损伤,以及导致此类损伤的事故或暴力情况”,又分为根本死因、直接死因、中介原因和辅助死因等(于晓军等,2010)。而我国法医病理学鉴定书往往把最后直接导致死亡的因素作为“死因”。由此可见,“死因”一词在法医学上是对所有引起死亡结果的因素的描述,其中不包含法律问题的判断。基于法医病理学鉴定的事实因果关系与司法审判的法律因果关系的差异性,法院不能依据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中记载的“死因”径直认定保险责任,亦不能根据法医病理学鉴定报告记载的“死因”直接认定保险责任,也就是说不能想当然地将法医学中“死因”当作保险法上的“死因”,否则将会造成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混淆。因此,在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死亡的案件中,被保险人死因是否明确并不能完全以医学报告为准,还应当综合各种证据综合判断死因。
在实务中,被保险人死亡原因有时处于完全无法查明的状态,如被保险人死于家中,公安机关出具“排除他杀”证明后,被保险人近亲属就将尸体火化,无法确定任何致死因素,此时就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不明。亦有案例中被保险人死亡原因并非完全不能查明,有时会有监控显示被保险人突然摔倒死亡,医院出具《死亡证明》记载“心源性猝死”,此时导致被保险人死亡的“条件”有“摔倒”和“心脏疾病”,但是无法判断被保险人突发心脏病后摔倒,还是摔倒后诱发了心脏病,因此无法确定各个因素对损害结果的原因力,以致无法确定何为法律上的原因,此时便是法律上因果关系不明。综上,“死因不明”的含义在法医学和保险法学之中并不相同。在法医学中,“死因不明”仅指事实因果关系不明,如果经过尸检就能够确定导致死亡的最后的因素,即为死因。而在保险法中,“死因不明”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事实因果关系不明,二是事实因果关系明确而法律因果关系不明。
(2)猝死的内涵厘清
猝死从字面含义来讲,是指突然的、出乎意料的死亡。“猝死”是否是指因疾病而死?目前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猝死是“因疾病而死”,权威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心脏病学会等,将其定义为“貌似健康的人由于身体内潜在疾病或重要器官发生急性功能障碍,导致意外的、突然的、非暴力性死亡”(林晓君,2012;韩长印、韩永强,2010)。有学者通过收集分析904例猝死尸检资料,发现猝死者多数可发现明显的器质性病变,或因冠心病,或因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无一不死于潜在疾病(杨清玉等,2008)。另一种观点认为猝死只是一种死亡的表现形式,属于损害结果的范畴,而非死亡原因。猝死的原因可能是疾病也可能不是疾病,不能将猝死简单等同于因疾病死亡(林晓君,2012)。此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从猝死字面意思来看,只是在描述死亡的急迫性以及不可预料性,并未隐含任何疾病要素。以上观点都没有错误,只是判断角度有所不同。第一种观点只是简单地从医学而非法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猝死是由潜在的疾病引发的,是一种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判断,不包含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判断。第二种观点是从保险法学角度出发,认为“猝死”应包括两种情形:由外界致害因素引起潜在疾病显露从而快速致死;或由自身疾病自然显露而突然死亡。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猝死的法律原因就是疾病。因此,法院在处理保险责任纠纷时,应从保险法的角度出发找出“死亡的法律原因”,而不能径直把相关证明文件中记载的“猝死”当作“死亡的法律原因”。
虽然死亡证明中记载的“猝死”并非法律上的“死亡原因”,还应进一步明确被保险人的死因,但实务中保险公司为提高理赔效率,同时也为缩小自身保险责任范围,常在意外伤害保险格式条款中附加“猝死不赔”的免责条款。那么此时法院能否绕过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径直以免责条款判决索赔方败诉呢?换句话说,“猝死不赔”免责条款是否有效呢?首先,“猝死不赔”条款并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497条、第506条以及《保险法》第19条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事由。一方面,“猝死不赔”条款不等于“死因不明不赔”,后者实际上是把证明“除外责任”的义务强加给了索赔方,而前者并未加重索赔方的举证义务,这是因为猝死一般都由专业的机构来认定,不需要索赔方自行搜集证据。另一方面,“猝死不赔”与英美法上“保险公司约定只承保由‘accidental means’造成的事故”类似,是对自己承保范围的限定,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更何况不论诱因为何,导致被保险人猝死的最后的因素一定是疾病,保险人只是在此情况下不予赔付,并非意在使得索赔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主张保险金。其次,虽然“猝死不赔”条款不具有上述无效事由,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有效,此时还应当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判断保险人在该格式条款订入合同时是否履行“提示+明确说明”的义务,并且在提示义务方面要达到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程度,在明确说明义务方面,要达到常人能够理解的程度,此种说明义务应高于一般的格式条款。如果“猝死不赔”条款符合上述条款要求,那么法院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此判决索赔方败诉。
(3)猝死与死因不明之间的关系厘清
猝死与死因不明的含义具有交叉的部分,但并不能将二者等同。首先,被保险人猝死并不意味着死因不明,在已经不能通过尸检或者其他手段确定死因之时,猝死案件就应当定性为死因不明的案件,运用死因不明时保险责任认定规则作出裁判,但可以确定死因时,就应当进一步判断死因是否在承保范围内。其次,被保险人死因不明并不意味着其是猝死,例如被保险人手术过程中死亡,而索赔方此时不知保险合同的存在,在尸体火化之后才得知遂要求理赔,此时被保险人不是猝死,但是死因也无法查明。理论研究中所谓的“意外险中被保险人猝死时保险责任认定”存在问题定性的错误,其本质上仍是对被保险人死因不明时保险责任认定的研究。
(二)责任认定逻辑顺序厘清
意外伤害保险中被保险人死因不明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事实因果关系明确而法律因果关系不明,如已查明被保险人事实上的死亡原因为“摔倒”和“心脏病”,但是无法查明两个因素之间的“引发”和“被引发”的关系。二是事实与法律因果关系皆不明,如被保险人死亡后未尸检即被火化,且无生前录像还原死亡经过,以致无法查明事实上的死亡原因。前者属于事实已经查明的情况,只需要按照意外伤害保险责任认定规则解决责任的归属。后者则属于事实真伪不明,仅依靠实体法规则无法解决责任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借助程序法的手段解决问题。因此若要全面解决意外伤害保险中被保险人死因不明时保险责任认定问题,便需要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进行制度的全方位构建。
但是,在实体法上意外伤害事故的认定中,有两种逻辑顺序:先判断因果关系,后判断法律原因是否属于意外伤害;先找出符合意外伤害的条件,后判断意外伤害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表面上来看第二种逻辑和侵权责任认定顺序一致,似乎更加合理,因为只有先确定意外是什么,才能判断意外和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但恰恰相反,此种判断逻辑在保险责任认定中是错误的,原因如下:首先,保险责任和侵权责任性质不同。若不考虑责任范围而只考虑责任成立层面,则侵权责任从行为人的行为角度出发判断其与损害的因果关系,而保险责任是从“损害”角度出发找与其有因果关系的事件,因果关系成立并不意味着责任成立,保险责任并非法定而是约定责任,责任范围由当事人自行约定,因而还需判断法律原因是否落入约定的承保范围,即判断法律原因是否属于“意外”。因此保险法与侵权法的责任认定逻辑不同,不能一味遵循传统的责任认定顺序。其次,此种逻辑顺序使得保险责任认定变得繁琐。若采第一种逻辑,先从事件中找出法律原因再对其是否符合意外性特征进行审查,免去了对其他事件是否具有意外性特征的判断。而采此种逻辑顺序就要对所有事件是否符合意外特征逐一审查,再在事件中找出法律原因,较为繁琐。最后,这种逻辑顺序会造成“意外伤害”认定与“因果关系”认定规则混淆。由于通说认为“意外伤害”包含“外来性”“突发性”“非自愿性”三个要件,“外来性”限制的对象是法律原因,若没有事先确定法律原因,又怎能判断其是否具有“外来性”?因此如果先从“意外伤害”构成要件着手,会使得人们误以为“因果关系”判断包含在“意外伤害”的构成要件之中。
正确的实体法上的保险责任的认定逻辑顺序应当是:首先找出具有事实上因果关系的“条件”,其次从“条件”中筛选出具有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原因,最后根据意外伤害认定规则判断是否存在意外伤害事故,考察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否“可归责”于保险人一方,以实现保险责任承担“归因”“归责”两个层次的区分。“归因”与“归责”的区分遵循了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基本逻辑,若不作此区分,保险法上因果关系的讨论将会陷入事实与规范相混杂的窘境(武亦文,2017)。
四、意外伤害保险中
被保险人死因不明之时责任认定
(一)实体法层面保险责任认定
1.实体法上保险责任认定——归因层面
“归因”解决的是危险同保险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武亦文,2017)。此时涉及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意外伤害保险中被保险人死因不明的案件中,虽无法通过因果关系认定规则确定法律上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在保险责任认定时没有适用余地。不同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对于法律原因认定的严格程度不同,进而影响到保险金的给付。而保险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有不同的学说,如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取“相当因果关系说”,而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取“近因原则说”,近来又发展出“比例因果关系说”等学说。以下通过对各个学说进行梳理比较,明晰意外伤害保险中被保险人死因不明时因果关系认定规则:
(1)保险法上因果关系判定规则梳理
一是“近因原则说”,源自英美保险法,英美保险法将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运用“条件说”从客观的“事件”中筛选出事实因果关系层面的“原因”,之后运用“近因原则”从“事实原因”中进一步筛选出与损害具有法律因果关系的“近因”(proximate causation)。而近因的判断方法经历了从“时间标准”(“nearest in time”test)到“效力标准”(the test of efficiency)的过程。近年来,英国保险因果关系理论从坚持“近因是唯一的”,转变为“承认复合原因(concurrent causes)存在”的立场,并运用帕特里奇规则、除外占优势规则构建复合原因下保险责任认定规则(John Lowry & Philip Rawlings,2005)。
二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又称“适当条件说”(Adaequanztheorie),源自大陆法系保险法,是指在一般场合下依照普通民众的观念,某种条件具有导致这种结果的高度盖然性,盖然性的判断取决于普通民众一般观念(江朝国,2010)。大陆法系构建因果关系二元体系的逻辑与英美法系不同,前者将因果关系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且在保险法领域仅涉及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江朝国,2010)。当多个条件均能通过“相当性”标准检验,但其中有的条件不在承保范围内时,保险责任的认定不无疑问。为此,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在采纳“相当因果关系”标准的同时,借重英美法系中“近因原则”对原因进一步筛选,进而判定保险责任归属(赵修稚,2018)。
三是“比例因果关系原则”,又称“分摊原则”,来源于挪威海洋保险计划,指当损害是由多个风险共同引起时,其中一个或多个风险不在承保范围内,则应根据每个风险对损失发生和程度的影响,将损失分摊到各个风险上。在传统近因原则或者相当因果关系判断标准下,保险责任认定呈现“全有”或“全无”两级分化局面,比例因果关系原则的引入改变了这一极端局面,有效平衡了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2)死因不明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一是因果关系层次划分标准的确立。大陆法系国家将因果关系区分为“责任成立因果关系”“责任范围因果关系”两个层次,通过缩小“损害”的范围以限缩责任范围。英美法系国家则将因果关系划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及“法律因果关系”,通过缩小“原因”范围以限缩责任范围。究竟何者为宜?答案是后者。正如前文所述,被保险人死因不明包括“事实因果关系不明”和“法律因果关系不明”两种情况,不同情况对应的责任承担规则不同,为保持逻辑前后一致性,应以后者为宜。且在被保险人死因不明属于法律因果关系不明时,死亡这一损害的范围已经明了,引发损害的原因为何却无法确定,因而重点应在于对引发损害的原因进行筛选,其中正蕴含了英美法系构建因果关系的基本逻辑。
二是因果关系判定规则的确立。在死因不明案件中,适用比例因果关系原则更加适当。一方面,比例因果关系原则符合现行法的规定。我国《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是对于比例因果关系的引入,司法解释中“被保险人的损失系由承保事故或者非承保事故、免责事由造成难以确定”意在指造成结果的条件有多个,既有承保、非承保又有免责条件时,无法确定何为法律上的原因的情况,指向的正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明的问题,“按照相应比例”实际上是按照法官对于各个条件作用力大小形成的心证比例。另一方面,比例因果关系原则有利于平衡双方利益。在法律因果关系不明而事实因果关系查明的情况下,法官只是对于哪一个条件属于“法律原因”很难形成内心确信,即使将多个无法查明作用力的条件均视为“法律上的原因”,此时应当运用帕特里奇规则、除外占优势规则等进行进一步的责任认定,最终仍得出“全有全无”的结论。不论全部支持哪一方,对于已经完成对案件事实进行举证的义务的另一方而言皆不公平。而比例原则的引入则可以有效缓解利益失衡问题。比例因果关系原则要根据各个原因的作用力大小确定赔付比例,看似不能适用于原因的作用力无法确定的案件中。但是实际上,比例的确定更多的是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证,即使双方当事人均无法进一步证明原因的作用力大小,法官也可通过在案证据评估原被告主张的条件对于损害的重要性的大小,进而按照心证的比例作出判决,这其实是对证明标准的降低。是故,在死因不明案件中适用比例因果关系原则,不仅能够与现行法相衔接,更是突破了传统的“全有全无”保险责任认定模式,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分配的公平,有效地定分止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实体法上保险责任认定——归责层面
归责是完成归因后的步骤。因果关系确定后,应当考察原因是否可以“归责”于保险人,即考察原因是否落入意外伤害保险承保范围。事实因果不明的案件中无法判断导致死亡的事件有哪些,更无从判断事件是否符合意外性特征。法律因果不明的案件具有判断意外性特征的必要,此类案件一般会存在多个引起损害的事件,需要判断哪些事件符合意外性的特征,以便通过《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确定双方当事人分担保险责任的比例。关于意外伤害的认定,学说纷繁多样且各有千秋,并未形成定论,简要梳理如下:
(1)“意外伤害”认定的路径梳理
一是原因结果二分说。此种学说由早期的英美判例法发展而来,并经历了从“原因说”到“结果说”的发展过程(Peter Nash Swisher,2007)。首先是“原因说”。由于英美法系国家保险公司将“意外伤害”分为“accidental means”和“accidental results”,且只承保“accidental means”所导致的伤害(王雁冰,2015),法官仅依保单的内容判定只要原因是意外的,不论结果是否为意外,均可认定为意外伤害。其次是“结果说”。由于原因说过度向保险人一方倾斜,英美判例法发展出“结果说”来平衡双方利益。结果说源于1889年美国Barry案,该说认为即使原因不是意外的,只要结果是意外的即可推定存在“意外伤害”,此时就算保单中约定了只承保“意外原因”的条款,保险公司仍需承担保险责任。最后是“意外就是意外说”。在Landress案中,美国大法官Cardozo提出“意外就是意外”的观点,不再区分意外原因和意外结果,只要有“意外”因素存在就是“意外伤害”,当双方当事人对于“意外伤害”的内涵出现不同理解时,应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
二是构成要件说。构成要件说多为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所采,如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即从法律法规中提取出“意外伤害”的构成要件,事实满足全部要件即构成“意外伤害”(张静竹,2017)。构成要件说中的主流学说是“传统三要件说”,该说为德国保险法所采,认为意外伤害包括“外来性”“突发性”“非自愿性”。其中,“外来性”是指引起意外伤害事故的原因必须存在于被保险人之外,而非内在身体过程所引发的(刘强、陈禹岩,2015),排除了自身的疾病所致的损害,这是与健康保险区分的关键。“突发性”是指致害原因快速发生且不可预料,包括“时间上的短暂性”以及“不可预料性”两个方面(刘强、陈禹岩,2015)。“非自愿性”又称非本意性,是指损害结果的发生并非被保险人故意所致。之后还有“传统四要件说”(该说为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所采,认为“意外伤害”包含四个要件:外来性、突发性、非本意性和非疾病性);“新四要件说”(该说认为应在传统三要件的基础上应再加上因果关系这一构成要件(黄慧鹏等,2002),“因果关系性”是指致害原因为损害的直接且单独的原因(江朝国,2015)。)而通过学说的梳理比较可知“传统三要件说”最合理。以上各个学说都是在“来外性”“突发性”“非自愿性”三个要件基础上进行添加,反有画蛇添足之效。原因有二:首先,“非疾病性”并非独立的要件,“外来性”恰恰强调引发损害的原因并非内在的身体疾病,“外来性”已经包含了“非疾病性”,且较后者而言更能准确体现“意外伤害”的特点;其次,“因果关系性”要件应被排除,由上文可知,“因果关系”是归因层面的问题,“是否属于意外伤害,落入承保范围”是归责层面的问题,不应混淆。综上,意外伤害的构成要件应仅有三项,即外来性、突发性和非自愿性。
(2)死因不明案件中“意外伤害”的认定
通过对两大法系学说的梳理,可以发现大陆法系的要件说更加符合我国实际,更有利于解决意外伤害保险的被保险人死因不明时保险责任的认定问题,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要件说更加契合我国保险实务。一方面,传统四要件的释义已经我国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之中广泛适用,也成为学者乃至普通民众对于“意外伤害”概念的通常理解,不宜骤然废弃要件说;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并不具有英美法系国家中保险公司事先约定仅承保“accidental means”引发的损害的背景,因此我国多数学者将其误译为“意外原因”。实际上“accidental means”并非指事故的近因,更恰当的释义应为“意外方式”(肯尼斯·S·亚伯拉罕,2012),意味着不论引发事故的近因是否为意外,只要方式不是意外的则不承担保险责任,实际上排除了近因原则的适用,大大缩小了自身的责任范围。法官一开始只是消极地根据格式条款的规定作出判决,由于普通民众难以理解格式条款的内涵,判决结果往往与投保人的预期不符,为了改变这种困境,才发展出“结果说”以平衡双方利益。而我国大多数保险公司并未将意外事故限定为必须是意外方式引起的事故,法院在认定意外伤害时与英美法系的逻辑出发点不同,仍须根据近因原则作出裁判,我国并没有适用“原因结果二分说”的现实基础。
其次,要件说更有助于与因果关系认定规则相区别。正因英美法系保险公司在保单中事先约定排除近因原则的适用,采原因说的法官出于对保险合同意思自治的尊重,没有根据近因原则作出裁判。这会使得采结果说的法官亦步亦趋,也忽略因果关系的认定。如在美国Barry案之中,被保险人Barry从四英尺高台跳下,因着地姿势不当导致肠闭塞,进而引发死亡。法官认为被保险人虽有意从高台跳下,但在此过程中出现了Barry无法预料的落地方式,此种落地方式引发了肠闭塞,进而导致了死亡结果,此种情况便属于意外伤害。但结果说的结论恐怕与常人的认知不相符,同时亦会对法官进行误导:只要结果是意外的,保险公司即需要承担保险责任,无须进行因果关系的判断。但若法官先进行因果关系的判定则会得出与结果说截然不同的结论。同样是Barry案,若适用近因原则,法官须先筛选出“从高台跳下”这一近因,然后以近因不符合“原因外来性、突发性”为由判决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若适用比例因果关系原则,法官也可以先筛选出“从高台跳下”和“出现意想不到的落地方式”两个条件,根据比例因果关系原则确定两个条件的作用力比例以确定保险金的给付比例,却仍不会得出由保险公司承担全部保险责任的结论。由此可见,较之原因结果二分说,要件说可以很好地区分“归因”与“归责”两个层次。
再次,要件说标准更加清晰。在英美法判例中不论原因说还是结果说都涉及“意外”因素的判断,仅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证,没有明确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如何判断原因或是结果是“意外的”?最终恐怕还要回归到要件说中“外来性、突发性、非本意性”标准之上。大陆法系的要件说各个要件的内涵及限制对象皆较为清晰,法官具有较为统一的裁量标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同案不同判”现象的产生。
最后,要件说更能平衡双方利益。例如,被保险人在车祸中丧生,尸检报告显示其因潜在心脏病而死,但是此时无法确定车祸引发了心脏病,还是心脏病发作导致车祸,因而处于法律因果不明的状态。如采纳原因说,索赔方实际上负担了完全举证责任,必须要证明“致死方式”是意外的,即需证明车祸引发了心脏病,而非心脏病发作导致了车祸,显然加重了索赔方的举证负担。如采纳结果说,索赔方只需要证明结果是意外的即完成举证,此时需要保险人证明“致死方式”不是意外的,是心脏病发作导致了车祸,其负担的举证责任过重。若采纳要件说,车祸和心脏病均属于引起损害的“条件”,索赔方只需证明存在车祸,车祸自然满足“外来性”“突发性”“非本意性”的特征,保险人只需证明存在心脏病这样的非意外因素。此时法官先通过自由心证对车祸和心脏病作用力大小进行评估,确定相应的比例,然后通过意外伤害认定规则认定“车祸”符合意外性特征,而“心脏病”不符合。最后根据“车祸”的作用力的比例确定保险金的给付比例,从而实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衡平。
3.小结
死因不明可分为“事实因果不明”和“法律因果不明”两种情况。基于“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二元区分,法律因果不明时法官应依其本身的法律认知并结合法律规定来决定,在事实因果不明时法官需依据当事人的主张与举证而为判断(卡尔·拉伦茨,2020)。是故,在法律因果关系不明而事实因果关系明确的案件中,法院先通过事实因果关系认定规则筛选出“条件”,根据在案证据判断各个条件对于损害的作用力的比例,再判断各个条件是否符合意外伤害“外来性”“非本意性”“突发性”的特征,按照符合该特征的条件对应的比例,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判决比例给付保险金。在事实因果关系不明的案件中,由于尸检即可确定具有事实因果关系的死因,是故死因无法查明的根本原因在于尸检不能,此时仅有过往病史或死亡证明中“排除他杀”等间接证据,无法进行因果关系和意外伤害的认定。当实体规则无法解决事实真伪不明难题之时,应转向程序法的证据规则进行进一步评判。
(二)程序法层面保险责任认定
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和证据提出的有限性导致的客观存在,亦是适用证明责任做出裁判的前提(曹志勋,2013)。意外伤害保险的事实因果关系不明属于“事实真伪不明”,实体法规则在解决此类问题之时难免捉襟见肘,此时应当转向程序法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1.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1条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一方应对该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一方应对该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意外伤害保险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亦遵循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
(1)索赔方的先举证义务
索赔方主张保险金的给付,其负有对“意外伤害事故”的首先举证的义务。但是学理上及实务中对于索赔方的证明责任承担限度有较大的争议,即索赔方要证明到何种程度,证明责任才能移转至保险人一方?根据《保险法》第22条可知,索赔方负有提供证明和相关资料的义务,未能履行则不能获得理赔。那么若索赔方履行该义务后,是否意味着已经完成了举证?有的观点认为《保险法》第22条也是对索赔方举证责任的规定,索赔方仅具有初步的、有限的举证义务,只要提供了其所能提供的资料证明事故的发生,且依照经验法则可以判定事故具有“外来性、突发性”的,举证责任就转移至保险人一方(王卫国、吕伟,2019;刘强、陈禹彦,2015);而有的观点认为此条与索赔方的举证责任无关,仅意在为提醒或督促请求权人在请求保险金给付时积极提供证明资料,而不含举证责任之意(岳卫,2010),其仍要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8条的规定,证明存在意外伤害事故,并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标准。
通过比较可知第一种观点更合理,理由在于:第一,后一观点会引起条文冲突且不符合《保险法》第22条的立法意旨。《保险法》第22条的表述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证明和资料”,意在免除索赔方对于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资料的提交义务,而第二种观点使得索赔方即使完成资料提供义务仍不能从举证责任中解放出来,这也变相架空了《保险法》第22条的条文规定。第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8条原则上以“高度盖然性”为证明标准,但亦规定:“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该条但书就是保险索赔方承担较低证明标准的法律依据,即索赔方只需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承担初步的、有限的证明责任。第三,由于人类认知和技术的局限性,法官只能通过证据的认定来无限地接近客观事实,此时便会出现两种疏漏:一是可能拒绝了当事人应得的救济,二是可能允许当事人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救济。只有这两个错误的成本或带来的负面效应相等时,维持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才是适当的(Tyree,1982)。在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中,由于索赔方大多数为普通民众,不具有保险人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经验,往往不了解如何搜集和固定证据,容易使得证据灭失,权利得不到救济,而基于保险法保护弱者的理念,应当适当减轻其举证责任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因此索赔方仅需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以其所能提供的资料为限。第四,索赔方的初步证明义务在实务中也有体现,如果索赔方在事故发生后能够及时提供保单、被保险人身份证明、被保险人生前体检报告以及保险事故处理单位(如医院、公安部门)出具的事故鉴定结论,法院即认定索赔方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就转移至保险人一方。综上,索赔方仅承担初步证明责任,若及时提供了其所能提供的证明和资料,即可推定存在意外伤害事故。
(2)保险人的指示举证义务
根据《保险法》第22条第2款,保险人认为有关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履行一次性的通知补充义务。对于保险人而言,此条规定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双重属性。从权利的角度来说,这是保险人控制危险及损失方式之一,若索赔方能提交却未提交相关资料时,保险人有权要求其补充提交,索赔方拒绝提交将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从义务的角度来说,若保险人没有及时告知索赔方补充资料或者没有一次性告知其补充资料,在索赔方提交的证明资料无法证明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与否时,不利后果应由保险人而非索赔方承担,因此更准确地说,保险人的指示举证义务是一项不真正的义务。此种义务对于索赔方而言,也是一项典型的举证责任减轻的事由。
(3)保险人的反证义务
在索赔方完成初步举证之后,举证责任即转移至保险人一方,此时由保险人对拒赔的事实和减轻保险人责任的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具体包括:(1)保险人主张履行了对免除或减轻保险责任条款的说明义务的;(2)保险人主张事故属于除外责任的;(3)索赔方未履行告知义务的等。
2.尸检与举证责任的关系厘清
在法医学上,若对突然死亡的死因持有怀疑的,为了确定死亡原因均应进行法医病理学鉴定(杨清玉等,2008)。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死亡原因无法查明(事实因果不明)根本原因在于尸检不能。那么尸检是否属于法定的义务?不利后果将由谁来承担?尸检不能的背后往往具有复杂成因:索赔方先尸体火化后通知保险公司出险;保险公司未告知尸检,导致索赔方未尸检就将尸体火化;保险公司告知尸检,索赔方拒绝尸检;索赔方与保险公司共同怠于尸检等等。因此不能单纯的将尸检认定为一项由索赔方或是保险人一方承担的法定义务,应当通过法律解释进一步明晰尸检与举证责任的关系,为司法实务提供更加精细化、合理化的裁判路径。
(1)尸检与索赔方事故发生通知义务的关系
尸检实际上决定了索赔方通知义务的履行期限。根据《保险法》第21条第1款规定可知,保险事故发生后索赔方应“及时”通知保险人,以便保险人及时调查搜集证据,以查明事故原因、损失程度,及时进行责任核定。这里的“及时”所指的期限不明,往往依靠保单约定的时间或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认定。在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死亡的案件中,法官经常会把“索赔方在尸体火化之后通知保险人”认定为未能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因而判决索赔方败诉。由是观之,在此类案件中通知义务的期限是较为明确的,应为“尸体火化前”。如果索赔方在尸体火化后通知保险人,致使尸检客观不能,则应当被认定为“通知不及时”,那么便应当根据《保险法》第21条的规定,自行对死因无法查明承担不利后果,不得请求保险金的给付。
(2)尸检与索赔方的初步证明责任的关系
据上文可知,索赔方的初步证明责任限于“其所能提供”的范围内,那么尸检是否属于此范围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尸检不在索赔方的初步证明义务范围内,因为基于中国传统入土为安的观点,同时基于近亲属对于死者的特殊情感,要求其同意尸检过于苛刻,不应将同意尸检上升为一种义务(中国保险行业协会,2021)。另一种观点认为,尸检落入索赔方初步证明义务范围内,若保险人告知其应当尸检以及拒绝尸检的不利后果之时,索赔方仍拒绝尸检,就应认定为未能完成初步证明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两相比较之后,显然后一种观点更为合理。首先,根据《保险法》第22条第1款,索赔方只须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资料和证明,这里的“其所能提供的”含义不甚分明。证明标准的模糊将会导致索赔方任意以“超出其所能提供的范围”为由拒绝提供证据,相当于变相免除了索赔方的举证责任,显然与保险人的合同预期不符。其次,如在保险人一方无过错,而索赔方拒绝尸检的情况下,仍由保险人承担责任就会诱发道德风险问题:索赔方知晓被保险人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但是若同意尸检查明死因便不能得到保险赔偿,因此故意拒绝尸检试图制造出死因不明的情况,进而得以获得部分保险赔偿。
(3)尸检与保险人指示举证义务的关系
索赔方配合尸检的前提是保险人对尸检及不利后果进行了相应的通知和说明,这就是保险人的指示举证义务的内容之一。保险人具有保险专业知识技能,其更熟悉保险理赔程序及证据固定方法,也更清楚死因不明所产生的拒赔风险,要求其承担通知尸检的义务并无不当。在此问题上还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在事实因果不明时,索赔方有义务查明被保险人的死亡原因,因此索赔方配合保险公司进行尸检应当被纳入证明资料提交义务范围内,属于法定义务而无须事先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因此上文中提及有法院以“《尸检告知书》是对原合同添加,未经过对方当事人同意不得订入合同”为由认为索赔方不承担尸检义务是错误的。第二,尸检的通知应当明确具体且附有对拒绝尸检的不利后果的说明,在索赔方同意尸检时应协助其完成尸检,否则即视为未完成指示举证义务,应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通过分析汇总可发现,保险责任承担也有内在的规律:尸检不能的原因往往是某一方违反了相应的法定义务,那就应当由违反法定义务的一方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如果双方均违反了法定义务,对死因无法查明具有一定的过错,那应当根据过错程度按照比例分担保险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按过错比例分担责任”的理论依据并非比例因果关系原则或《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按比例心证规则,而是一种用于促进主体积极履行义务以使证据信息尽可能固定的归责与制裁机制(胡学军,2013),是与有过失原则在保险赔付中的引入。
五、结语
针对实务中频频出现的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死亡原因不明的情况,在现行法框架下,通过对裁判案例的整理和分析,已初步形成针对意外伤害保险被保险人死因不明时保险责任认定的具体裁判标准。
第一步,判断是否有合同约定。若保险合同或保单中约定了“猝死不赔”条款,同时医院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鉴定报告写明死因为“猝死”,法院就应当根据《民法典》《保险法》相关条款,从格式条款的效力出发:如果“猝死免赔”条款符合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要求且无其他无效事由,那么虽仍属于死因未查明的情况,但法院应尽量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判决索赔方败诉;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猝死免赔”条款,或约定了“猝死免赔”条款但并非猝死,又或“猝死免赔”条款无效,那么法院应当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第二步,判断死因不明属于事实因果关系不明还是法律因果关系不明。若属于法律因果关系不明而事实因果关系明确的情况,此时往往已经通过尸检或者其他手段确定了具有事实因果关系的死亡原因,那么法院应当通过比例因果关系原则以及意外伤害认定规则,综合在案证据,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的规定判决比例给付保险金。若属于事实因果关系不明的情况,则需要进行下一步分析。
第三步,判断索赔方是否履行及时通知义务。在被保险人死因不明的情况下,索赔方“及时”通知的标准应为“尸检前”。如果索赔方将尸体火化后再通知保险公司,则应视为未履行事故发生通知义务,索赔方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法院应当判决索赔方败诉;如果索赔方在尸体火化前通知保险公司,那么法院应当进行第四步分析。
第四步,判断保险人是否履行提示举证义务。保险公司在接到出险通知后,若认为索赔方提供的资料不足以证明意外伤害事故时,应当及时出具《尸检告知书》并详细说明拒绝尸检的不利后果,同时应当帮助索赔方完成尸检。保险人完成此项义务则对死因无法查明不具有过错,此时仍由索赔方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若没有完成此项义务则具有过错,但是不能径直判决索赔方胜诉,还应当结合索赔方的过错综合判定,此时应进行第五步分析。
第五步,判断索赔方是否履行初步证明义务。索赔方应当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资料,包括尸检证明,因此索赔方若怠于和保险人沟通配合尸检或拒绝尸检则可认定其存在过错。结合第四步分析结果,如果索赔方没有过错而保险人具有过错,则视为索赔方已经完成举证,举证责任转移至保险人一方,保险人应当承担全部的保险金的给付责任;如果索赔方有过错而保险人不具有过错,则索赔方未完成举证自行承担不利后果,保险人不承担保险金的给付责任;如果双方均具有过错,则应当按照过错的程度依比例分担保险责任。
以上便是对于意外伤害保险中被保险人死因不明时保险责任承担问题的分析及认定。抛砖以引玉,希望本文对理论研究与司法裁判有所助益,以更好地定纷止争,维护司法的公正与权威。
编辑:于小涵
中国保险学会
构建保险大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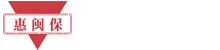






支付宝转账赞助
支付宝扫一扫赞助
微信转账赞助
微信扫一扫赞助